我在县公立医院做肿瘤专科培训医生(oncology fellow) 的第三个月正赶上风清气爽的十月金秋。某个周末科里安排全体医生去山上度假村开会,留下我与上级W医生值班。W是新近从“地段院级”私人诊所跳槽过来的中年医生,矮墩墩的个子,五官扁平,人随和但话不多。

周六上午一起查完房,他回家,我留下写病历。没过多久内科打电话来叫紧急会诊。我按着病房号寻到12楼。出电梯见一大铁门占据整个走道,通过四周镂空的栏杆瞅见里面往上还有一段楼梯,顶端放一小桌子,两边各坐一名荷枪实弹壮如铁塔的警察。他们指指我身边墙上的开关,我按下开关后小铁门应声打开。上楼一看,“老天!原来真是监狱……” 警察带我走到一间牢房前,打开铁锁,让我进屋,自己则无声地站在我身后门边。我闭了闭眼适应屋内暗黑的光线,见床上躺着一个19岁的瘦弱病人“小A”。奇怪的是他腰部往上的一半比下身肿了两三圈,脖子不见了,脑袋比西瓜还大,胳膊比腿都粗,双手肿得握不起拳。也不知他能否看得见我,因为他两眼已肿得无法睁开,喉咙里似乎有声音发出,但因嘴唇与舌头的肿胀词语根本无法分辨。脐部之下则完全没有水肿。他当时血压只有80/50,心率120,呼吸近30。我对警察说,”这样危重的病人必须马上转去ICU! ” 他点头示意我出去,随手反锁上门。
一小时后我在楼下ICU又见到了”小A”。他已经上了呼吸机,昏迷不醒,身上插满了管子。与其他ICU病人不同的是他的双手双脚都被铁镣铐在了床框上,床旁椅子上坐着那个武装到牙齿的警察。“这有必要吗?” 我指着镣铐问,“我们不想冒险(we are not taking any chances)”,说完他转过头示意对话结束,他的肢体语言告诉我再纠缠下去没我好果子吃。
两小时后加急的CT和化验结果出来,病人得的是睾丸癌,已转移到各级淋巴甚至肝脏和肺。罕见的是腹膜后巨大淋巴结压迫致肾脏血供受影响,病人已完全无尿,肾功能正急剧下降。另外他的两臂深静脉布满了癌栓,引起上腔静脉综合症(头颈部极度肿胀),如果不及时缓解会导致腔室综合症,大面积组织坏死,以致短期内死亡。
虽说我做住院医时的老师们给了我扎实的内科基础,但这样罕见并危重的病例我敢保证那些医生自己也未必见过。我紧张地拨通了W医生的电话,详细报告了病史,然后深吸口气,等待他的指导。两三秒钟过去,话筒那头还是一片沉寂。
“Hello…”
“哦,我听着呢…唉,实话告诉你吧,这种病例我从未见过,其实我在二十多年的医疗生涯中只见过一例睾丸癌。对不起,我帮不了你,you are on your own.”
卡擦,挂了!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You are on your own- 你自己解决吧。这人可真胆大包天!作为上级医生,不亲自到场处理如此急诊已经罕见,然而在得知详细病情后不提供建议,不寻找资料,不联系同仁,只区区几个字把责任完全推给刚开始专科训练不到三个月的下级医生,简直闻所未闻!
难以遏制的怒气让我面红耳赤,真想把话筒砸个稀烂。那时没有手机,只有值班医生才有BB机,因此根本没办法找到在山上开会的世界级权威-我们主任。
怎么办?怎么办?离周一还有36小时,无所作为的话恐怕小A十二个小时都挺不过去。马上做化疗肯定不行,因为他功能微弱的肾脏不能代谢有极大肾毒性的药物;况且就算马上化疗上腔静脉癌栓也不可能在几天内消除…19岁啊,就这样让他死吗?这时我真正体会到”热锅上蚂蚁”的滋味……
被愤怒冲昏头脑几分钟后,我抬腿慢慢走回系办公室,一面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思考治疗方案。我找出所有的教科书,翻遍每一条睾丸癌病情症状,可书里即便提到也只三言两语的描述,完全没有对付方法。最后在内科书中血栓治疗上有一句说到静脉插管溶栓,但没有具体做法(当年介入放射学尚未普遍)。
我抓起电话接通放射科找值班医生,当班的恰恰是那每天三点不到就溜回家的懒散的C医生。怎么这么倒霉?这下完了……没办法,沉住气咬牙介绍完病情,忐忑地提出静脉介入溶栓的想法,做好了挨一顿骂或受一场讥讽的准备,谁料话筒那头传来温和且带鼓励的话语,“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我愿意试试,但你要理解有大出血的可能,况且效果完全不能保证,老实说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那是自然,我理解”。 几小时来极速跳动的心总算慢下了几拍,至少有了个可以一试的方案。小A没有任何家属,C医生几分钟后就让人把他接去放射科了。
我坐在办公室干等,胡乱翻着专业杂志,一小时后护士电话说他回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回ICU。他左肘部插着输液管,里面是小剂量的TPA溶血药,C医生说要吊过夜,明早看看效果再决定下一步。我仔细查看了他身体其它部位,没有出血的迹象。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这才意识到午饭没吃,晚饭点也早过了。
周日早上回到医院,发现他的左臂肿胀消了一大半,导尿管里居然还有了几毫升尿液。我禁不住喜出望外,太不可思议了!下午C医生又让人把他接去,拔了左边的导管,放导管到右臂,同样留管过夜。
晚上电话不断。病人血压不稳定需要大量药物维持,呼吸机氧分压已到100%(不能再高了),肾功能还没有好转……我一面告诉护士尽量调节药物支持,同时担心着明早主任回来是否会同意我的做法,也许应该先用化疗?化疗透析同时做?思前想后几乎一夜未眠……
周一七点出头先去ICU 看小A, 以便在主任八点上班时汇报。他还是昏迷不醒,不过右臂肿胀消了许多,升压药剂量不用那么高了(说明血压稳定些了),氧分压需求少了些,肾功能至少没再恶化。刚想暗自松口气,却突然发现他脖子里的淋巴结似乎大了不少,说明癌症的恶性程度相当高,生长速度极快。莫非我没第一时间给化疗错过了治疗机会?这可怎么好?
心慌意乱地来到主任办公室门口,坐立不安地等到八点没见影,八点十分也没动静。秘书说可能去泌尿外科了。等不及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拨通了泌尿科电话,还真在那!
“Jia, 有急事吗?我过几分钟就回办公室,见面再说吧”
“我需要现在就说”,没等他接口我就急速汇报了病史,待讲到周六下午与W医生的那段对话时,突然间两天来积压在心里的愤怒恐惧忧虑和委屈一齐涌上胸口,百感交集下流利的叙述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哽咽,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淌下。“我是来受训练的fellow, 想不到会让我孤身一人对付从未见过的病例,没有任何支持,怎么会这样,这是啥鬼地方?!”
“……” 对方深深吸了口气 “哦,他那么说is what he said” 听得出这几个字是咬着牙说的。“….没关系,现在好了,我回来了,一切由我担着,我马上过来我们一起去看病人“。在楼下见面时他看见我还红着眼睛,忍不住笑,
“以前你和我拍桌子吵架时没想到会哭吧?”
“我没真哭,只是觉得太不公平!” 很想问他准备怎么处理W医生,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还是病人重要。
详细看了病历后主任对我的做法表示赞同,说在所有可能性中还是这个最保险也最合理,部分溶解了两臂静脉及上腔静脉中的血栓后肾脏血流改善,给现在马上需要进行的化疗创造了条件。随后他说把化疗拆开来小剂量做,常规三天的量分在七天打,这样不正常的肾脏能够承受,还可以根据肾功能的改善每天调节剂量。
……
-4-1024x768.jpg)
四周后小A 的肿胀完全消失了,淋巴结摸不到了,肾功能也基本恢复正常。只是长期使用呼吸机加上卧床不起,他那些本来就不发达的肌肉就更萎缩了(两条腿真像铅笔般细),所以还用着呼吸机,也还需要镇静剂,否则他就乱抓乱拔管子。就这样他的四肢还是被镣铐天天铐在床上,床边凳子上也天天坐着个荷枪实弹的警察。这时我才有闲心想到,是每个监狱病人都这样还是小A犯了重罪?那究竟什么罪呢?
一个月的县医院病房轮转结束了,我把小A交给下一轮同事,自己去对面私立医院继续学业。同事们日间相遇甚少,寒暄匆匆,竟未有暇问起小A的病情。
再见小A已是四个月后重新轮回县医院病房时。他早已出了ICU, 被安排在开放式的护士工作台后转角处一个5-6平方的单间里。警察坐在锁上的门外。
进门一看,差点认不出来。身上的管子拔得只剩一根PICC,浮肿全消,脸和五官都清晰了,除了消瘦的脸庞及锁在床栏杆上的四肢外,看上去与正常人无异。只是他脸上毫无表情,见人来眼皮都没抬。而此时作为医生的我却是万分欣喜-这个曾让我度过惊心动魄48小时的人居然活了过来!按捺不住激动我详细对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的危重病情和治疗时的矛盾。“看到你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CT 复查各处肿瘤全部消失,简直难以置信,我太为你高兴了!“
手舞足蹈的我突然意识到床上的人仍然毫无反应,头朝里对着天花板,眼神呆滞。难道他不懂英语?我用西班牙文问“你听懂吗?讲英语吗?” 身边的警察插嘴“他的英语流利”。我只能默默走向门外。
我知道警察是不允许对外谈论监狱病人的,但兴许他们平时与跟前来往的护士闲聊会漏出只言片语来?我悄悄叫住管他的护士问,知道犯啥罪吗?护士摇头走开,“那么年轻,终身监禁可惜了…”
两天后他该出院了,我去给他拔PICC (插在肘部的深静脉管用来打点滴,可以留几个礼拜或更长时间)。拔完后向他道别,“很高兴你能出院了,几周后你来门诊部随访时再见”。回答我的还是一片沉寂,猛然间他回头与我四目相对,这一眼让我终生难忘,他眼中只有难以误解的两个字:仇恨!
二十多年来这个病例像个旧疮疤,天阴时常常浮出脑海,抓挠不着的隐痛令我不安。
他为什么会有那仇恨的一眼?是像我儿子所猜“恨你救活了他”?是因为他要在狱中痛苦终生而仇恨整个社会?…或许,或许就像电影“哭泣游戏the crying game” 结尾男主角讲的故事里那个蝎子,原是“他的本性”?
我该不该废寝忘食竭尽一切地去救他,明知他是个重罪犯?知道他不会感恩?无数次扪心自问答案还是”yes!”。医生的职责是救治任何病患,男人女人,东方人西方人,穷人富人,好人坏人…一视同仁-希波克拉底誓言里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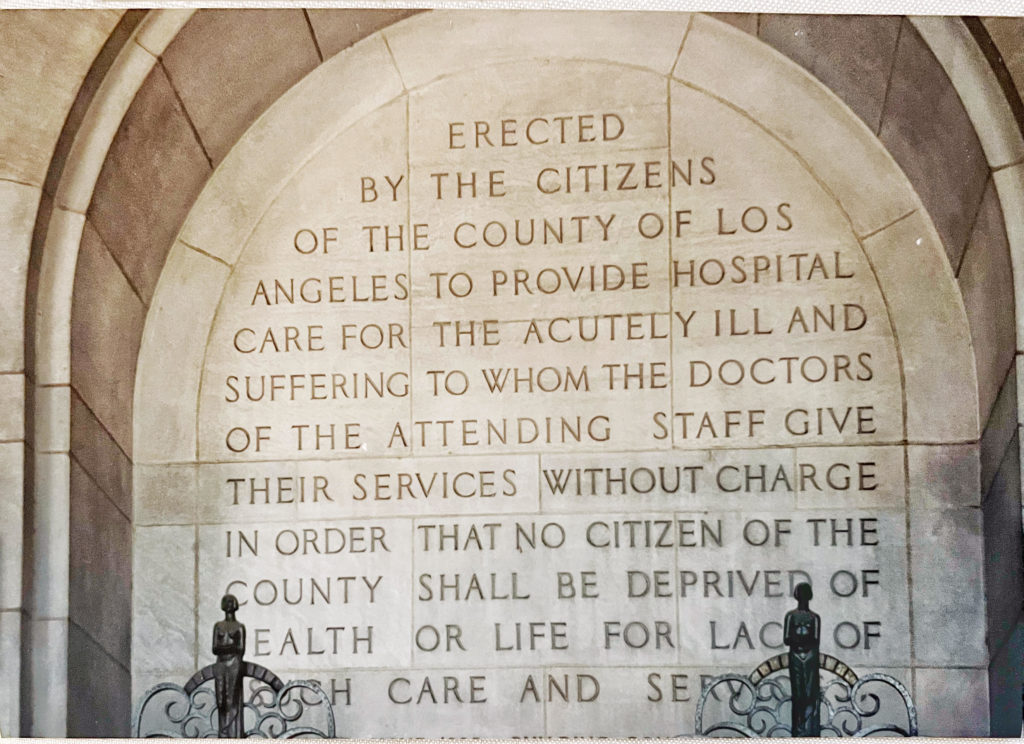
要感谢小A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医学上经历了如此的狂风暴雨后其它病都算不上病了,凶险程度比不上,孤身作战的机会就更少了,一般情况下几位同仁同心协力事情就好办得多。于此经历里我也对人性有了更深的感悟,比如三点回家的并不等于平庸医生,其实C医生才是勇于尝试真正救命的英雄;貌似老实善良之人(W医生)在关键时刻竟能无动于衷见死不救;而平时自诩为正义化身的主任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也不敢“冲冠一怒”而把W医生开除…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虽说那48小时还历历在目,但小A的名字已经模糊,他的相貌也已淡出,可如果有一天再相见,他还给我那充满仇恨的一眼,我相信自己能坦然地迎接。
作者:毕佳